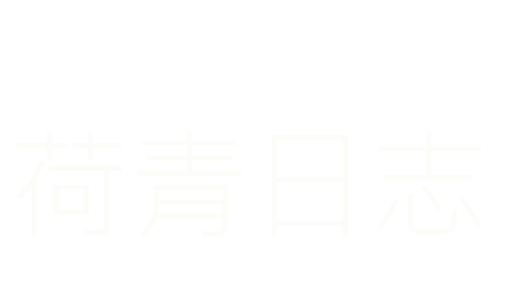关于花
原想把题目写成“花之恋”,并以爱的名义开头,但我在表达感情方面并不擅长,更重要的是,我不是一个轻易就感情外露的人,这倒有些像含羞草了。所以,我要用我的含蓄、矜持和内敛来面对现在窗外那一排风中摇曳的清秀的小黄花以及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在一个人很寂寞的时候,脑子里会闪现出某些很深沉的句子:在每一个有阳光或风雨的日子里,我都会默默地注视着你,十年,二十年……你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双眸子里呈闪着怎样的光芒。
虽然对花有这般情思,但说实话,我见过的花并不多,可我有勇气说什么是博爱。这得从那年春天说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个人呆呆的坐在公车里,不想动更不想说话,静静地看着窗外退后的街景和匆匆的人群,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只有我一个人是唯一的静止,不为什么特别的而失落,只是泛泛的空荡起来。忽然,烂漫的粉色桃花隔着车窗跳入眼帘,飘逸而轻柔如浮云,如鲁迅先生提到的上野的樱花,是要勾人心绪的。在好不容易换过了整个冬天之后,蓦地遇到这般绚丽的景象,我心知荡漾便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生活的美好的希冀柔柔的涌上心头。黑暗与光明,颓废于进取间的跨越总要伴着泪光才深刻,正如那是我湿润的眼。
花是有灵魂的,要不然怎么能引起我心灵之震动,我也尽心所有的花都如是,所以话是值得爱的。也正是由于每枝花都飘着灵,花才能象征人的品行。
且看那风姿,意识里虽不很明确的反出“高贵”“淡雅”“纯洁”等形容词来,也满腹的这样认为着。因此,文学作品中花木就常有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我略知一二。早就以为无非是写一个卖茶花的女子,后来才知道那个女主人公只是手里常拿着茶花罢了。她叫玛格丽特,这名字很好听,是一种花的名字,想着这纯洁,可玛格丽特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名妓。这几千的深意可耐人寻味;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是我所喜爱的,而我认为最精彩的片断要于花有关。那天女主人公冒着大雨坐黄包车,风雨中遮掩庇护间柔弱之意横生,更可贵的是拿手中的一只百合,呵,好一个风雨之百合,将女主人公的形象衬托得淋漓尽致;《梧桐雨》中的沈岩对何俊兰说:“当你骑着车子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觉得眼前的就是一株娇美的兰。”沈岩本是园艺家,也难怪他说出这富有诗意的话语,兰的形象与人物形象充分结合就全在这句话了。
眼里常见着花,心里常感染着花,难免有些关于花的希望。一日,凭着自行车独自去乡间,借着山水排遣抑郁、寄托理想,在文人名士们是常有的。我的不辞劳苦,顶着个日头满野地里跑,也不过想,尝一尝野花的野味,若能挖几株回去,也算解了心头那股子难耐的渴望劲儿。可这儿,只是满眼的绿绿的水稻和飞驰而过的火车,且不论那花,就连陶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之景都不曾见,何来欣赏之闲情?尚无巷中之犬,却有一老鼠,竖直端坐于道中央,挡住了我的去路,这姿势在小狗身上倒见过,在老鼠却是头一回。我只好打道回府,将此次窘困的乡间行将给人听,一位老者说我是“生小出野里”,才落下此般野性,人和花一样有特定的生长环境、有特定的个性,所以对于老者的话我并不反对。
等到我长大了些,野性渐退了不少,竟崇敬起岳飞、文天祥等英雄人物,时常豪气地自言自语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看书上说梅最有风骨,想必是如雨雪飘零的冰山一般,也就总是吟着梅:“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角吹彻。清绝。影也别。知心唯有月。”我还知道林微因在一片散文中曾提到过梅,徐志摩说落在皑皑白雪上的梅的花瓣是十三龄童的热血,我喜欢这种说法,梅本来就是有生命的。
去年年末在某山村里度过,正赶上那里过年,情景并不入室前想象的那般热闹,倒是连绵的白雪覆盖的山峦使得这个冬天愈加冷清凄凉,有人告诉我西山里有座破庙,庙里却有上百株的梅,花事正盛,我心动了,可是,在这样一个阴冷的天气里翻山越岭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接而脑中浮过那百株梅的模样,“也好,不管它是冬天。”我念叨着。
——因为那百株盐分的生命屹立在寒风中招唤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