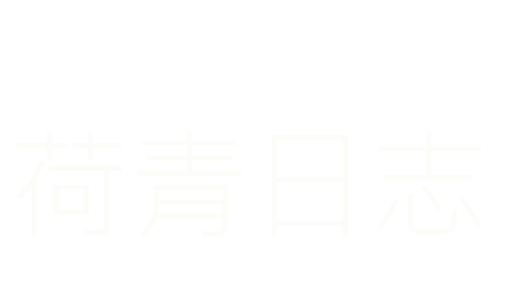成长的屐迹
谷粒刚刚在发芽——看起来那么娇嫩,那么脆弱——它会穿过黑土,穿过石块。
——阿·托尔斯泰
一如既往,我用指尖拨弄着他走之前留给我的那把古色古香的吉它,坐看天即有淡粉红变成深绛紫,再由深绛紫变为淡粉红,感觉着这一抹抹温馨的浪漫的颜色。我记得他说过当我遥望大自然时就一定会看到他在为我画画。不知不觉中,有泪盈眶……
我从小就管他叫大哥哥,最初童年的印象中,除了一个他送的布娃娃(早被妈妈送人),就再没别的什么了,而一切的变化都源于一种不经意的美丽,那一张花好月圆的相遇。
我们这栋楼的顶上有个不大却向月的平台,平日少有人迹,我曾为此不解的问过妈妈。他说那种萧索与冷清是早为现代人所厌弃的,甚至很少看到有人去洒衣服。其实我知道:他们大多醉心于相拥而立,翩翩起舞的朦胧与迷离,或是电子游戏,VCD的精彩刺激,而每每立于此地的我却感到领受了大自然丰厚的馈赠,这便是最能润泽心灵的人间圣境了。我喜欢蓝色的平和,更疯狂地爱这里的宁谧,这一片被月光温柔者的心灵栖息地,因为我知道白天一脸稚气未脱、开朗活泼的我,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找回自我,回归一片空灵。而随着高中课业负担的加重,我已许多时日没有抽身去坐坐了,这实在不能不算是一种悲哀。
仲秋时分,夜晚格外的田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知名的花儿吐露的馥郁芬芳,天那边的云彩显得有些害羞,时隐时现,好像不太愿意出来与我打个照面,而我尚能望见那一轮我所熟悉的圆月,就已十分地满足。于是,我便披着洁净的月色,独个儿利索地爬上了久违的平台。说来也怪,我只是踱了没几步,便一下子就找回那份失落已久的醇美的心境了。我真庆幸在这样喧嚣浮华的俗世中尚能寻觅到这一处圣静之所,有意识地环顾四周,确定无人光顾,心中便窃喜起来。
我是极爱音乐的,平时我总是哼一些欢快大众的港台歌曲,而事实上我便钟爱那些缠绵悱恻的英文经典老歌。我自诩也有一副不赖的嗓子,在这四下无人的圣地,当然应该一展歌喉。我没有去想这一唱是否会破坏纯然的寂静,只是扯着嗓子,动情地唱那一典《UNCHAINED MELODY》。
我无意解释为何在我唱至一半停顿下来,竟起了一阵沉郁优美的间奏,是吉它声!我慌乱的循声而去,终于在平台入口处寻到了他的踪影。
“你……,大哥哥!”我一眼便认出了他,心却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脸上想必也泛起了红晕。
“我来了好久了,见你很专注,便没敢打扰你。你唱得很好,为什么不继续唱呢?我替你伴奏吧!”他的声音磁性而动人。
我没有拒绝,大方地接受了他的提议。我很用心,跌宕起伏地唱,在末尾还加上了别具一格的真假声处理。他的指法挺熟练,而那吉它抑或是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音色并不算太好,但我们的配合实在是默契至极的。这不能让不让我为此愕然,却不得不信服上天巧意的安排。
星盏渐渐点亮平台,一切显得挺和谐,而我和他竟相对无语了。她用一双又深又黑的眸子注视我,而我迎着他温暖的目光,也傻傻的看他,却全然不知为何,仿佛我们从不曾相识,便要如此悉心的捕捉对方的每一个细腻的眼神了。
“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他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
“为什么?”我疑惑地望着他。
“白天的你是蹦蹦跳跳的,现在的你是沉静脱俗的,可怎样的你才是真实的你呢?”他的语气很奇怪,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我不知道他何以有这样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是否在白天邂逅过他,所以只能缄了口,后又尴尬地朝他笑笑。
“我想为你画张画,你能做我的模特吗?”我不假思索便应允了。
他点点头,有些拘谨的从一大堆画纸中抽出一张,选了支专业的素描用笔,没有对我有什么别的要求,除了随意地抱着吉它,自然地遥望天空。我没有能看清他是如何用笔的,不过我以为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是无法成就什么好画的。
他将画纸轻递给我,而我惊呆了。难道他真是借了月亮的灵光吗?我真有那么美吗?我仔细地揣摩着这幅作品,心想原来这么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线条竟能如此完美的组合在一起,像是偶获至宝一半,爱不释手。我深知他功力不凡,因为我父亲就是沪上知名的画家,过去我也跟他学过画画的,他教过我如何鉴别作品是否是佳作,可就是他也一定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就一副好画的。
正当我惊异于他的神速时,风泄漏了这个秘密。他没有打招呼,趁我们猝不及防时,重重地打了个喷嚏,吹散了那一叠画纸。我赶忙上前帮他捡起,竟又一次惊呆了。每一张画纸上不都是我吗?怪不得他画来如此得心应手呢?我先前的疑问由此被解开了,却陷入了一个更深一层的迷惑中。
他没有向我解释什么,恭敬地用双手接过那一叠画纸,坦诚地笑笑,说:“其实你早就是我的模特了!你很特别,白天有一种朝气蓬勃的美,夜晚平台上有一种清雅绝尘的美,真的!”
我以不及的当时脸上是如何表情的,只知良久没能说出话来,心里滋生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动。在心目中的我是那样美好,何以见得?
“谢谢你!”这是我迟钝后的反应。
“谢我什么?”我明知故问。
我诡秘的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我们相视而笑,刚才的疑惑也一下子变得不重要起来。我只是想一直浸着迷人的月色,倾听他带磁的声音,与他促膝交谈,甚至可以不理会时间已经很晚了。
“你画得很好,以后想当画家吗?”我定睛望着他。
“我只是想去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校学习。”他淡淡地说,但我看得出他的眼中有一份执著的信念。
“你赢定新购的。”我的声音轻而幽,却饱含着真诚的祝福。
时间就像一个沙漏,总在我们不经意间滑过了,不知谁家的钟声颇有韵律的敲打了十二下,像是在提醒灰姑娘该回家似的。而那一瞬间,当我们听着悠悠的钟声响起时,竟又一次默然了。他追着这我的目光,我想可以避开,可做不到。彼此的目光就这样维系着,似乎过了一个世纪,我收回了目光。
“我要走了,太晚了。”我低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明天我们一起去写生,好吗?”他真挚地问我。
我很快地点了点头,便向他道别的,随后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却发现脸颊已涨得通红。不知为何,那一晚我第一次失眠了。有一刻我以为自己身在梦境中,于是起身坐起,不敢水下,而他的影像竟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
我是目送着那轮我所熟识的圆月落下的,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新生命的诞生,耀眼夺目的光彩昭示着新的一天的到来。这是周末的一个钦臣,万物复苏,大地很友善的朝我点头,我便又活跃起来,尽管昨晚并未睡好,眼圈还是黑黑的,挺像大熊猫的,但与风儿赛跑又怎么可以错过?
我一如既往地坚持晨跑,再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他如约而至,肩上还斜着画具。“走,跟我来。”他一把拉住我的手,飞快地朝背离人群的方向奔去。我本该挣开他的手的,可我没有,而是温顺的随他去了。
那是一个很有些复古色彩的八角亭,在城市的确不多见,我暗暗思忖为何从未刘新国。他也该有不平凡的故事吧,我揣度着。
“你看,这是小时候刻的呢!”她的语气很天真,让我暂忘了他整整大我四岁。
我循迹望去,那根大柱子上隐隐刻着“×××”与“×××”的字样,字迹十分稚拙。我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可如何也忆不起是谁在何时饶有兴致的雕刻的。
“你还记得吗?”他心急地问我。
“我想不起来了。”我要了摇头。
他似乎有些失望,一本正经地说:“我以一直没忘记。那时你五岁,我九岁,这些字还是你要我刻的,瞧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噢,我想起来了。”我失态地叫得很大声,“在这儿你还送了我一个布娃娃呢!”
“对啊,那个布娃娃还在吗?”他追问道。
“被妈妈送人了。”我轻叹了口气。
“可惜了。可惜了。”他感叹了两句,便不作声了。
“你不是要写生马?这里很好啊!”我出了个好主意。
他没有犹疑,从肩上卸下画具,慢慢摊平卷曲的画纸。
“刻画什么呢?”
他没有硬卧,而是专心致志的做起话来。这一次我真有机会好好看他画画了。这不禁使我联想起童年是跟爸爸学画,那种神往的姿态,那样沉醉地用笔,都是爸爸曾有过的。而我的心里是有一些些忌妒的,他似乎忽略了我的存在。我专注地望着他,却全然不知他究竟在画什么。他正得意的遨游在艺术殿堂里,又怎知我灼热的眼眸所蕴含的真情实感呢?
“好了,你瞧怎么样?”他好像又记起身旁有一个我。
“啊?这里哪里有叶子呀?”我很纳闷。
“你看,那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五米开外的一片瘦小而枯落的叶子。”
“你画的叶子比它到好几倍呢,别哄我了!”
“你看过日本著名风景画家东山魁夷的文学作品《一片树叶》吗?”
我像摇头翁似的摇着脑袋。
“作者曾在院里看到一片茶褐色的枯叶从树枝上落下来,而在通知,另一个幼小坚强的芽儿,孕育着新鲜的生命,晚强地诞生了。这既是生命轮回的道理,你明白吗?”他耐心地给我解释。
我极为细致的思索这,最后竟也顿悟出生命的真谛了。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对吗?一片枯叶凋零的同时一定有一个小芽儿会诞生,小芽儿长大了,就成了你画的这片叶子,是吧?”我俏皮地说。
“你悟性挺高嘛!”他夸我时眉飞色舞,非常有趣。
“可你知道我为什么画这片叶子吗?”
她问得有些玄,我只是想刚才那样摇摇头。
“为你,”她稍作停顿,接着说,“为你能快点儿长大啊!”他的目光清澈而柔和。
我没做反应。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而我懂,懂他的良苦用心,并为之深深震撼。
“请记住,当你要看大自然时,就一定会看到我在为你画画!”他轻握我的手,像宣布特大新闻似的对我说,“我在等你长大,你知道吗?”
我在那一刹那几乎是呆滞的,只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思维骤然停止,好长间隔我才回过神来,只是一反常态地点了点头。
我深切的知道:他希冀我快快长大,而我又那么不愿意让他失望。我喜欢他,从平台回来就已确信无疑了,我还憧憬着会和他有幸福的未来。而又不知为何,我竟也直觉到这一切终将成为弥足珍贵的记忆,在岁月的辗转中留下屐迹……
在他眼里的我不再是昔日那个抱着布娃娃到处要吃要喝的孩童,却始终是不谙世事,目光短浅的小女生。他惟恐我知识掌握得不够丰富全面,或是理解会有偏差,所以拼命的替我恶补,几乎成了我的家庭教师了。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察。我了解他,他是那样深地宠爱着我,生怕我遭受任何委屈,经受任何挫折,我也从没见他对其他女孩子好。
我竟也害怕其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了,因为无论如何我不愿意做温室中的弱苗,我真想大吼一声:“让我做暴风雨中的松柏吧!”但我没能说出口,因为那样他就会走,也许永远的离开我,去比利时,她父母那儿。他之所以还没走,是为了我。我很自私,不愿他离开我。
我如何才能向这个世界说明最后我是怎么想通的,因为说出来是极少有人相信的,而那却是真真切切的发生了。不值一提,有非同寻常。
他早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了,周围的朋友都为他对于艺术独特而深刻的理解而暗自叫绝,就连父亲也称赞他是当代画界不可多得的颇有灵气的菜籽将来是会大有前途的,却又低声道:“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不去比利时进一步深造呢?”我的心不由地一酸。
我反反复复的体味着父亲的话,竟在一念之间开释了。这说来是如此轻易的,其实却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我觉得所有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勇敢的决定而作准备的……
从他为我素描时,我便已确信他不是一般的庸人,而属于浩瀚无际的艺术海洋。在那里他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翱翔,展翅高飞,就像是天边那只神采奕奕的海鸥,永远深情地眷恋着澄明开阔的大海。我确定他并不属于这里,更不是与我。可我为他高兴,为他骄傲。
大哥哥,有朝一日等你达到梦寐以求的心愿,倘若惦记我儿飞回此地暂作停歇,并且愿意与我分享那些只属于你的神秘的人生历程,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别无他求。
真的,你不必回头,去飞吧,去圆你心中圣洁的梦吧!请相信,在我与你挥手作别时是坦然的,尽管你始终牵引着我的视线,直到你飞走了,我才像过去那样收回目光。而我也始终不愿意告诉你——我长大了。当此刻的你是否听到我双手合掌为你虔诚的祈祷呢,你真能感应我吗?
如今的我已明白这份份扰扰茫茫无涯的人海中,也许我们终将擦身而过,你有你的方向,我也会我的。而在同一平面内,即便我们只是两条永不能相交的平行线,又怎能否认这不是爱的忠贞呢?何况在那时空无声的流转中,我们曾经如梦似幻的相交过,共同走过一段美丽而难忘的岁月,也是你使我懂得了成长的含义,领悟了生命与爱的真谛,我又怎能不心怀感激呢?
天空依旧高悬那轮晕月,我怀抱着那把他留给我的老吉它,遥望着清纯如昔的大自然,仿佛云端便出现了他的身影。在那里,他在为我画画……